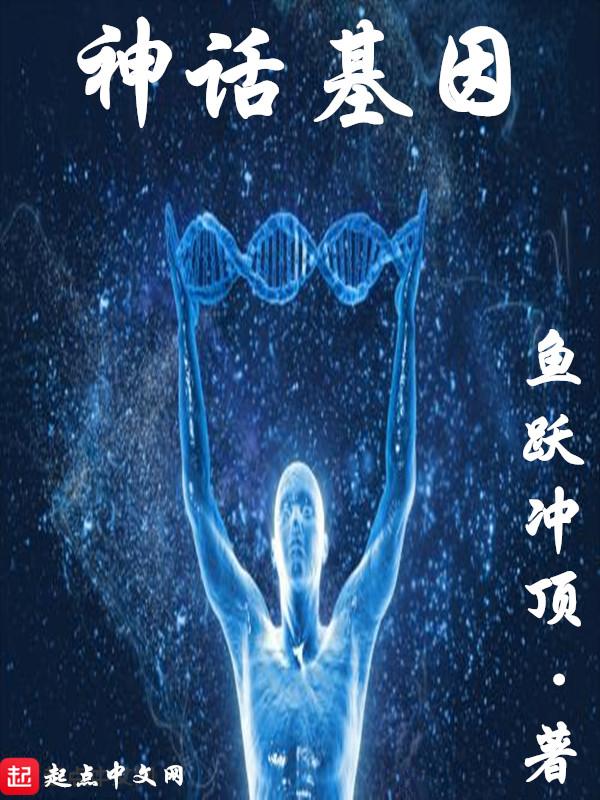秋天小说>皇室笔记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八刀。他给我抹药包扎,道:“安王好勇气!”可是我却想,完了。原来以为手臂上的伤,我自己看得见,再如何疼也不怕,等弄完手臂上的伤,疼得麻木了,也就不怕腰上疼了。可是原来真的疼是不会麻木的。若我还有力气说上一句话,我一定辩解。他已经开始清理我后背被血水黏在一起的贴衣。他就要拔刀了。我想,元奚白啊,我就是这么怕疼的人。老军医按住我的肩膀,我竟能感觉得到他的手已经放在我的箭身上,猛地一痛……不疼、不能疼。我死死咬住毛巾,感觉得到血水从箭口流出。疼,疼得好!他的刀在血水从翻找腐肉,割了五刀,方上药包扎。我已经听不清他说什么,只知道箭疮还在流血。心中一壁觉得自己丢脸,死死非要扯上她;一壁又暗自高兴,这拔箭的痛,我毕竟过来了。于是放心睡过去。醒时天光明亮,听得外面军士噪喊之声,想起来看看,却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力气。环顾帐中宁静无人,军中应该没有大事,这样一想,又沉沉想睡。应该是拔箭之后又发热起来。丢脸,真丢脸。再醒来时天还是亮的,身上有出汗之后的冷劲。正要坐起来,帐门一开,进来的是温师集。“你们回来了?”“是。”他把我扶坐起来。“山口之战可打了?如何?”“打了。乃美可汗从固特山退出,果真往乌拉特那山口逃亡,被李将军堵住掩杀。乃美底下的大酋长大多率众来降。这次,加上上次在绥武道,李飞雀将军共掳获五万余人。而杨将军在固特山一战中,斩首万余,获俘虏十余万,牛羊牲畜几十万,乃美的几个儿子、亲信多在固特山战中死。特厥彻底败了。”“那乃美呢?没有抓到吗?”“没有,他逃脱了。”“逃往何处,杨李有派军追击吗?”“没有。乃美可能是想逃往河西。不过灵州那儿派军北上逼近了。这几天我们也都在等灵州的消息。”我沉吟,“今天是几日了?”“二月十六日,大王已经昏迷多日了。”我还在世,却竟然错过了红玉的第一个忌日。二月二十八日,传来消息,说乃美投奔了他的弟弟康矢执。二月二十九日,灵州道行军总管程树金引兵逼近,要康矢执交出乃美。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帐中吃药,桑梓抚掌大笑:“乃美休矣!不日我等可归长安!”其实许多特厥贵族已经被送往长安了。特厥男女人口暂时安置妥当,李飞雀也开始准备回并州,杨道长也跟我提过一次回去。这种情形,回长安就是这么十几天的事。李杨两人在西北经营多年,若是他们可以不回长安,可是我却有什么理由不回去?!我把药碗往地上一掼。桑梓吓了一跳。愣了许久,默默收拾了出去。我躺在榻上生气。这一路来病得半死不活,难道终究还是要活着回长安么?桑梓换了一服药,仍然在帐中炉火边煎着,边开口道:“这样一幅药,要是在战争吃紧,百姓贫乱的年代,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天生烝民,应当爱惜。臣昔日流至长安,遭逢变故,不堪受辱,未尝没有轻生的念头。可是辗转颠沛,看到漠南之地,天地广阔,胸襟也为之一开,再也没有那样的念头。就算如何艰难,但是能看见这样的艰难——幸运的话也会挺过去——就是造物者的旨意。也是到了关外之后,才亲眼看到世之战乱、百姓贫苦,才开始顿悟佛家常说的慈悲。大王一路急行军过来,虽然亲履战阵,未免没有时间好好观赏漠南天陲的雄壮风景。现在战事已经确定,军中安稳,如果大王有精神,不如多出帐看看。一来可以暂时忘却心中块垒,二来俯仰自由,知天地之变。”那天以后,只要得空,我便在野外放马徐行。陪同人。三月六日,乃美带着数骑从康矢执军中遁逃到荒谷,康矢执连夜把他追了回来。一部分军勇开始收拾归乡。十几天以后传来消息,三月十一日,灵州道行军总管程树金破了康矢执,生擒乃美。这一日陪我闲逛的是桑梓。我们走了四五里,看不到营地,四下没有什么人烟。桑梓忽然问:“塞外漠南天高地阔,使人胸襟自开。可洗去大王心中的忧愁?”我说:“你怎知我心中有无忧愁。”桑梓笑了笑,“臣少时偶遇一个胡人,他告诉臣一个道理:心智坚强的人,未必每个人都能看出他的坚强;但是那些懦弱的人,却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的软弱。老子曾说过圣贤大智若愚,庸夫大愚若智。但是人本身不是圣贤,都是以本色示于人前。臣倚靠这个道理判断过很多人,没有失过手的。大王在病中,是最软弱的时候,许多事情,臣侍奉左右,就算想不知道也不行了。长安来的家信大王没开封就直接烧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王心中忧愁深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