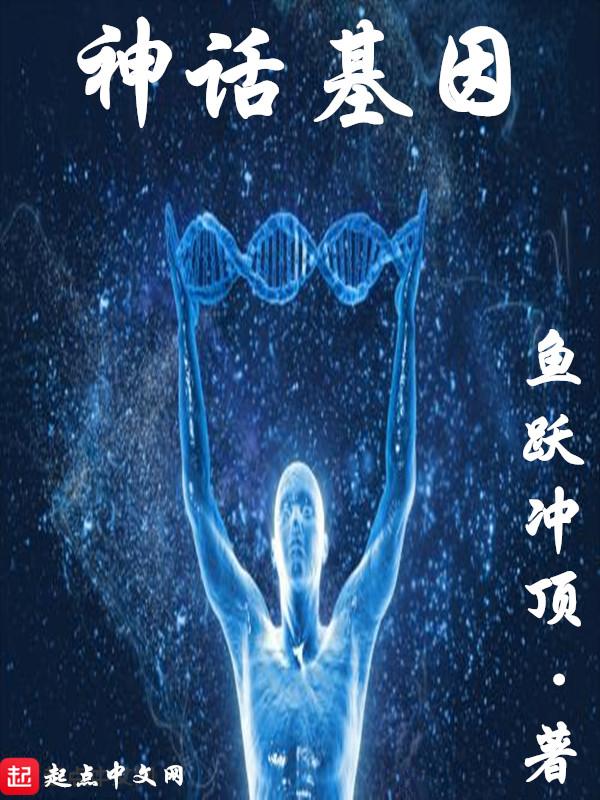秋天小说>祝你今夜梦不到我 > 第7章(第2页)
第7章(第2页)
四个多小时拍下来,黎羚自觉精神状态还算稳定,无非是变态怎么说,她就怎么做。
但旁边的工作人员,已是一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压力怪状态。
摄影师眼里爬满红血丝,每场间隙争分夺秒滴眼药水。化妆师一脸英勇就义地扑上来补妆,几把刷子挥舞得虎虎生风。
又一条拍下来,金静尧还是不满意。
“你的脸没有吃到光。”他说。
黎羚假装自己已经累到听不懂人话,非常无知地问:“那我要怎么做啊,导演?”
她以为他会和之前一样,不作任何回应。
然而金静尧静静地看着她,说了一声“抱歉”,径直站起身。
黎羚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向自己道歉。
直到她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男人朝自己俯下身,手指碰到她的脸,并没什么怜惜地托起她的颌骨。
尽管中间还隔着一张桌子,她依然感受到被阴影压下来时,那种难言的危险。
他的手指还是冰冷的。冰冷而刺痛,令人呼吸一滞的触感。
“就这样。”金静尧说,“别动了。”
黎羚的呼吸本能急促了一瞬。
陌生的气息,连同他的视线,像一场倾盆大雨,将她从头到脚笼罩。
他坐了回去。
她遵照他的指示,又演了一次。
在年轻男人的注视之下,她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舌头、眼睛和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
当黎羚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清晨的光线,从侧边的一面小窗户里照了进来。
这是近乎于奇迹的一刻。
晨光笼着她的侧脸,将面庞都照成金溶溶的一片。如同晨雾中的原野,洗去一切夜的沉痛,朝阳在她的眼底升起。
金静尧说:“可以了。”
她听到对讲机里,副导演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还夹杂着其他人隐隐的欢声。
黎羚像被抽掉骨头,烂泥一样趴在桌上。
被折磨了一整晚之后,她感觉有点不真实,努力地抬起半张脸,问金静尧:“导演,我这次表现怎么样?”
他语气很淡地说:“光线很好。”
黎羚没太听明白她的表现和光线有什么关系。
副导演走了过来,喜悦地汇报这一条的光影简直绝了,称赞导演真是料事如神,今天的日出和预料之中分毫不差。
黎羚:“……”
“导演,您要拍的是日出吗?”她忍不住问。
金静尧:“嗯。”
那你,为什么要,半夜两点,把所有人,都,叫起来,呢。
有些人凌晨两点把剧组拖进破剧院,足足排练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