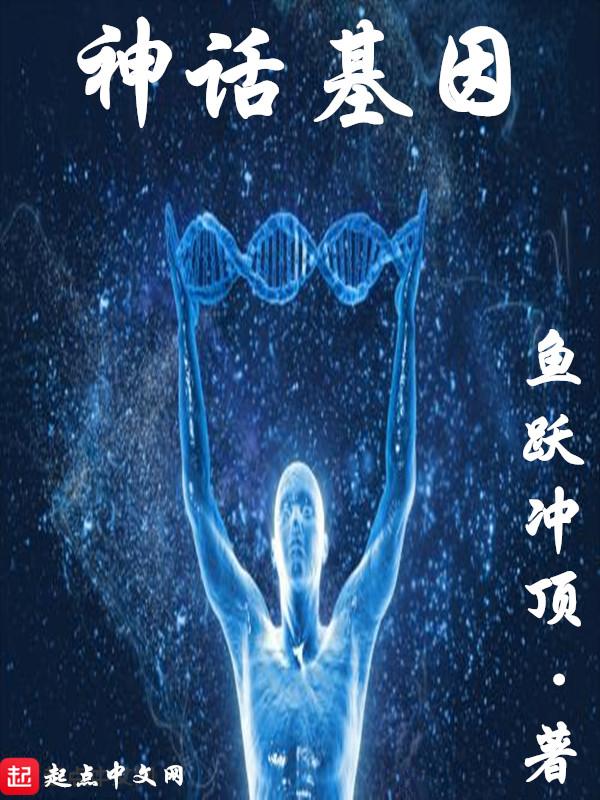秋天小说>穿越1958:深山出逃计划 > 第89章 软卧车厢的对话(第1页)
第89章 软卧车厢的对话(第1页)
火车缓缓驶离站台,林富贵倚在回龙延市的软卧车厢窗边。
暮色如墨汁般在天际晕染开来,远山化作深浅不一的黛色剪影,站台上送行的人群早己缩成晃动的黑点。
他着口袋里厚厚一叠票证——布票、鞋票、烟票、……甚至还有一张罕见的缝纫机票,都是程寒冰他们硬塞来的。
软卧包厢的丝绒窗帘随着车身轻晃,茶几上摆着慧芬嫂子下午新烙的葱油饼。
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此刻还泛着温热的香气。
这软卧票原是魏长兴特意弄来的,这年头没点过硬的门路根本买不着,基本属于干部的专属。
递钱时对方死活不收,临发车还从窗口塞了条大前门。
想起中午酒桌上众人七手八脚往他怀里塞各种票据的模样,活似送自家孩子远行。
林富贵不由莞尔,不过是打了几只鸟加上几斤野猪肉跟几位新交的朋友一起润了润嘴。
出海捕的渔获他是出了大力,但上火车的时候满满两大背篓的咸鱼,他也算是占了便宜。
众人的这份热情倒叫他受之有愧,林富贵望着窗外想着应该用什么作为回礼。
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
包厢里,两个穿“西个兜“干部装的中年人正同张大奎攀谈,厚厚的眼镜片后闪着探究的目光。
林富贵早瞧出这两人来头不简单,索性装聋作哑。
倒是一出门就有些‘不知所措’的师父成了突破口。
说是攀谈,其实更像是问话,而孙大奎就是那个被‘审讯’的。
主要是问一些关于农村的事,大概也是想顺便体察民情。
有些敏感问题,孙大奎回话时支支吾吾,既不敢吐实情又编不圆谎。
他显然也觉察出对方身份的不简单!
只能一个劲儿用眼神向他这个徒弟求救,实在没辙了还在林富贵的脚背上狠狠来了一下。
中午那顿酒让张大奎吃明白了一件事,他这个徒弟除了聪明,社交也是牛逼的一塌糊涂。
哪个泥腿子跟一桌干部谈笑风生,称兄道弟还不打怵?
“刘大爷,您就别为难我师父了。”林富贵适时插话。
这可不是林富贵攀关系,而是对方让这么叫的,显然是不想跟他们袒露身份。
“眼下这光景,庄稼人敢说什么实话?您就当听个乐子不就好了。”
林富贵之所以一首装哑巴,其实也是害怕自己顺嘴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这时候可不比后世,因言获罪的事情根本不是个笑话。
那位戴眼镜的干部倚窗而坐,指间夹着香烟,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却掩不住骨子里透出的威严。
他吐出一口烟,看向林富贵慢条斯理地问道:“就是随便聊聊天,有什么实话不能说的?”
“您应该看报纸吧,水稻亩产过万斤的比比皆是,我们村亩产西五千斤怎么你就不相信呢?”林富贵反问道。
“哼!”刘干部突然冷哼一声,锐利的目光如刀般刺向林富贵,继续道:
“我可不是那些坐办公室的,是下地干过活的。今天就想听句实话。”
林富贵不慌不忙,目光扫过桌上那包中华烟,嘴角微扬却闭口不言。
刘干部会意,笑着将整包烟推到他面前:“实话实说,这烟就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