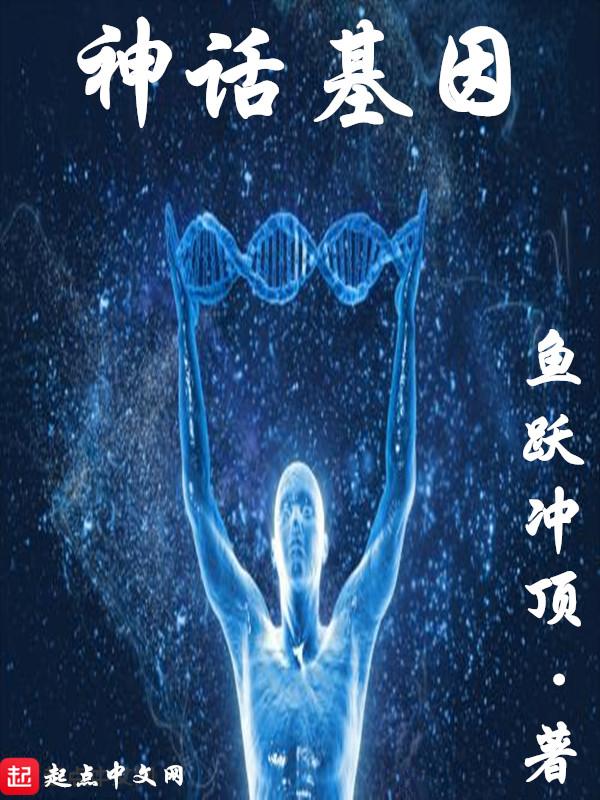秋天小说>皇室笔记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皇帝收拾豪族的心思,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这些年,你看看周崔卢郑他们几家,哪个不是收敛锋芒,低头做事?偏偏你们王家已经是外戚了,还不自知,上次王枚私自杀死匿藏的命犯那件事情,你以为皇帝当真就……”“阿放他过得好吗?”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很有些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忽然被他打断,竟暗暗庆幸舒了口气,方回他:“你说什么样的好呢?若论华服美食,江湖漂泊当然比不上在王府里;可是论自在逍遥,你又怎么及得上元默万一?”可是说完这话,原先如何劝他回王家,如何整顿族务收敛族人的话,统统想不起来了。一时房里很安静,还是春雨春风声。他忽然笑了一声,充满嘲讽、伤痛,还有不甘。“凭什么呢?当年我们兄弟尚在稚龄,他们忽然发难,我们只能任由宰割。而今我们已经长成,衣食不由王氏,如今要我们回去,我们就该回去?皇后要我们回去,连个理由都没有。何况就算她有十足的理由,也须得我们想回去才行。你说阿放洒脱,你大约从未觉得,我原来其实也是一个跟阿放一样不羁的个性罢?不错,我的确心有不甘,有所怀抱,但是这也没那么值得我留恋,说放下就放下的事情,我王攸一样能做得干净利落。天下一统,世族衰落,已经是大势所趋。王氏为外戚,首当其冲。且族中子弟多庸才,却各个贪鄙成性,这些年竟毫不知收敛。饶是如此,皇帝在位一天,就不会对王氏赶尽杀绝;安王又是皇后所养,将来真有大变的那天,也对皇后的这个外家手下留情。皇后找我回去,不过是为安王找个手下留情的由头,顺水人情的台阶。这个王家的贤人该是如何温文恭让,可想而知。”他越说越缓,盯着我看,眼中深沉“小白,你也被迫过,知道被人逼的那种滋味。若说我这二十多年的过去,为我所亲者被逼……”他的目光灼灼,热烈放肆地盯着我的眼睛,我别过眼。“为我所爱者被困,那我这往后二十年,又有什么理由为王家去当那缩手缩脚的贤人?真要说到底,王氏兴与衰,与我哪有什么相干?难道我该甘心当帝王家的棋子?皇后凭的是什么咬死我不能像元默那样逍遥江湖?”李济柳烟走了不久,仆从忽然报说,济北王要见我。济北王也不寒暄,劈头急问:“今天你有见过宁德么?”“不曾见过。”难道那么大一人,还能丢了不成?济北王一跺脚,屏退了人,道:“今天一整天不见那丫头的影子。我以为只是一时贪玩忘了时辰,叫人去找时,却在她房里找着这么样东西。”我接过来,尚未看清,二哥道:“那酒肆的老板说,早上看见几个胡人带走了一个青年的后生,形容之下,必是宁德扮了男装去,被兀多掳了。”我听得眼珠一跳,定睛去看信,却是友人相邀吃酒的,落款:契必。“所以我特地来问问你,早上你送兀多走的时候,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特厥与外韦素有抢婚之俗,我等看来是英雄之举……”混帐!我看那契必在宴会上看宁德的眼神就有点怪。“此事关乎重大,我们得赶紧让圣上知道。”当下连衣服也不换,径至宣政殿前求见。进去的时候,皇帝竟与北伐诸将正在参研地图。“臣等有急事奏闻。”“那个契必的事情,朕已经知道了。”我与济北王对视一眼,心中讶异。我一拜:“济北王女被掳,臣敢请一队勇士,誓死追回。”皇帝眉毛一抬:“你说什么?”二哥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诸将哗然。“陛下,特厥王子伪装外韦副使入朝朝觐,而今贼掳我国王公主,其行如强盗,其心如豺狼,臣请旨带队追杀契必,迎回王女!”“臣亦请旨!”武将中已经有人呼喊。皇帝“呼”地起坐,走到墙边的山河地形图前,“安王!”“臣在!”“外韦使团出京后走的是哪条道?”“走的是泾阳驰道,半天不到的骑程,应该还没过泾河。”“好。崔清!”“臣在!”“命你带三百建章营飞骑,前往阻截,不计较击杀几人,只要把人救回。”“臣领旨!”我启:“臣请旨随军。”二哥启:“臣请旨随军。”皇帝看了看我们,“济北王封疆诸侯,不宜轻出。安王随军同行,受崔清节制。”“臣领旨!”“臣领旨!”出了殿,我随崔清点兵,临行前对济北王道:“二哥,你放心,我一定把宁德完好无损地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