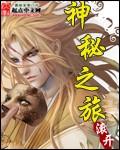秋天小说>春色满棠 > 第449章 亲征北月国(第3页)
第449章 亲征北月国(第3页)
万里之外,敦煌壁画上的李元朗画像,眼角忽然滑下一滴颜料,宛如泪痕。
如今,天下已有三百余座忆名坛,每一座都植有棠树。春分之夜,灯火连城,诵名之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浩瀚人海。
而最初的那株老棠树,依旧挺立在书院东阁前。它的树皮更加皲裂,年轮更深邃,仿佛整部人间记忆都刻在其内。偶有风雨之夜,附近村民称能听见树中传出低语,细听之下,竟是无数名字接连响起,绵延不绝,如同一条永不干涸的河。
有学者试图记录这些声音,耗时三年,仅得片段。其中最清晰的一句是:
“柳阿婆,六十八岁,疫中守村医,药尽后以草根续命,最后一日仍为孩童敷伤。”
录音当日,南方某山村突降甘霖,枯井复涌,村中老人说:“这是阿婆回来了。”
更奇者,近年每逢春雷初动,棠树渗出的金色汁液中,不仅生出四色花芽,偶尔还会凝成微型石碑状结晶,上刻陌生名字。书院弟子不敢擅动,皆供于归名潭畔,待春分时一一诵读。
专家破解其文,发现多为史书无载之人:奴隶、婢女、流民、乞儿、无名战士、失传技艺的匠人……他们生前卑微,死后无坟,却因某种神秘力量,穿越时空,抵达这棵神树之下,求一声“被记得”。
于是人们终于明白:
这世上从不存在真正的无名之辈。
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
只要还有一棵树肯为他们开花,
他们的名字,就会在风中流传,
比王朝更久,
比石头更坚。
某个无星之夜,少年沈明远守于树下,忽觉肩头一暖。回首不见人影,唯有衣上落了一片四色花瓣,形如手掌,轻轻覆在他肩头。
他没有害怕,只是轻声问:“是先生吗?”
风穿过枝桠,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像是回答,又像是安慰。
他笑了,仰头望着那棵苍老而倔强的树,低声说:
“您放心,我会一直听下去。”
那一刻,远方群山静默,天地无声。
然后,从北境到南海,从西域到东海,千千万万个角落,同时响起细碎的回应??
有的是母亲哄睡婴儿时的呢喃,
有的是老兵抚摸墓碑时的低语,
有的是学生朗读课文的清脆嗓音,
有的是恋人耳畔的温柔絮语……
它们汇聚成一股无形的声浪,穿越时间与空间,最终落在棠树梢头,化作一片花瓣的轻颤。
那颤动如此轻微,
却又如此坚定,
仿佛在说:
我在听。
我在听。
我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