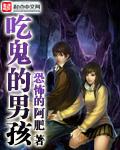秋天小说>咒禁山海 > 第三百八十九章 绛珠仙草 你大抵是倦了连心肝也不舍得予我(第1页)
第三百八十九章 绛珠仙草 你大抵是倦了连心肝也不舍得予我(第1页)
咚!咚!咚!。。。
看到这位天仙般的少女,王澄的心脏像是被电流击中,剧烈跳动了起来。
少女从头到脚简直没有一处不美,关键是每一处都长在他的心尖尖上,甚至比宴云绡、沈如意两位姐姐更加熨帖,更。。。
拾壹站在归忆原的最高处,望着那片如血般红艳的莲池。春风拂面,花瓣随风飘起,像无数细碎的记忆在空中飞舞。他手中握着一支旧竹笛,正是拾玖生前最后吹奏的那一支。笛身已有裂痕,却仍温润如玉,仿佛还留存着她的体温。
他已经在这里站了三天三夜。
不是守灵,也不是哀悼??他知道拾玖从不需要这些形式。她早已说过:“我不怕消失,只怕你们不再提起我的名字。”所以,他来此,并非为了告别,而是为了延续。
第一夜,他吹响《守灯谣》。音符落入池水,激起一圈圈涟漪,每一道波纹都映出一段画面:一个母亲教孩子背诵家训;一群少年围坐在老者膝前听讲先辈抗灾之事;一位盲眼说书人用沙哑嗓音讲述“忘忆之祸”中的十八藏书者……那些记忆并未消散,它们只是沉入人心深处,等待被唤醒。
第二夜,他取出碧玉笔,在虚空中写下拾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记即可赎。”字成之时,整片归忆原的红莲同时绽放,花蕊中浮现出微光,如同星火点点升腾。远处村落里,有孩童突然惊醒,喃喃念出从未学过的诗句;边境哨所中,老兵无端泪流满面,想起三十年前战死同袍的名字。
第三夜,他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风声、水声、叶声。然后,他听见了。
千万个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轻柔而坚定:
“我记得。”
“我讲过这个故事。”
“我奶奶告诉我,不能忘了拾玖。”
那一刻,拾壹终于明白??拾玖没有死。她化作了人间的回响,成了每一个愿意记住的人心里的一盏灯。她的存在不再依赖形体,而是扎根于亿万次讲述之间。只要还有人说起她的名字,哪怕误传一句言语,曲解一段经历,她就在那里,静静聆听,微微一笑。
他缓缓起身,将竹笛轻轻放在通天木下。随即转身,走向南方。
三个月后,南方瘴林深处传出异象:一座荒废多年的古庙突然自燃,火焰呈青白色,持续七日不灭。当地人不敢靠近,只远远看见庙顶升起一道光柱,直贯云霄。待火熄之后,庙中仅存一块石碑,上刻两行字:
>**“记忆非锁链,乃薪火相传。”**
>**“若你记得我,请也记得你自己。”**
拾壹的名字自此淡出朝野议论。有人说他已入深山闭关;有人说他化身游方说忆人,背着布囊走遍天下;更有传言称,每当某地出现大规模失忆怪症时,总会有一个穿灰袍的青年悄然现身,手持断忆刀残片,口中低吟《守灯谣》第七章。
但无论他在何处,各地“野忆堂”皆奉其为精神宗师。他们不再追求统一史观,也不再执着于所谓“真实全貌”。相反,他们开始收集矛盾的说法、冲突的记忆、甚至荒诞的传说。因为在实践中,人们渐渐发现:正是这些差异与争执,才让记忆保持鲜活。
譬如北方某村,两位老人对同一场雪灾的记忆截然不同。一人说当年全村靠吃树皮活命,另一人却坚称朝廷及时赈灾,米粮堆满祠堂。野忆堂录忆官并未判定孰是孰非,而是将两者并列记录,并附注:“此二人曾共抬一副棺材,送走七个饿死的亲人。”后来学者研究发现,那年确有赈灾令下达,却被地方贪吏截留。百姓既未全然绝望,也未真正得救??于是记忆分裂成了希望与苦难两个版本。
这便是人的记忆本质:它不完美,常带滤镜,掺杂情感,却也因此真实无比。
十年过去,第九颗星终于完全点亮。
那一夜,整个九州都能看见天际浮现奇异星图:八星环绕,第九星居中,缓缓旋转,宛如开启了一扇无形之门。但并无灾难降临,反而全国范围内爆发罕见的集体梦境??数以百万计的人梦见自己牵着陌生人的手走过黑暗隧道,尽头是一片开满红莲的原野。有人认出那是归忆原,而站在花海中央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正低头整理一本破旧笔记。
醒来后,许多人发现自己竟记起了幼年遗忘的片段:母亲哼过的摇篮曲、父亲背自己看灯会的脚步声、祖母临终前紧紧握住的手……更奇特的是,一些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在街头偶遇时竟脱口而出对方童年的小名。
科学无法解释,唯有录忆官们低声感慨:“渊门未开,心门已通。”
又五年,西北边陲建起一座新式学堂,名为“逆钥书院”。其入学第一课不是识字算数,而是让学生闭目静坐,回忆自己最不愿面对的一段往事。有人痛哭失声,有人沉默良久,也有孩子勇敢说出:“我爹打仗回来变了个人,夜里总喊救命,我妈说他是英雄,可我觉得他好可怕。”
老师不加评判,只问一句:“你还爱他吗?”
当孩子含泪点头时,教室墙上的一面铜镜忽然泛起涟漪,浮现出一行古老文字:“**唯信不疑,方得始终。**”
与此同时,东海海底的石阵彻底沉没。经年累月的洋流冲刷,加之亿万次记忆共鸣的震荡,那座曾孕育忘魇的“记忆坟场”终于崩塌。断裂的玉柱化为齑粉,扭曲符文随泥沙掩埋。渔民偶尔回收残片,却发现上面不再显现痛苦影像,反倒浮现温馨场景:一家人围炉夜话、学子金榜题名、夫妻携手归乡……
考古学家推测,或许是某种集体意志重塑了遗迹的本质??曾经埋葬痛苦的地方,如今成了孕育希望的温床。
而在南疆某座无名山谷中,一间茅屋静静伫立。屋前种着一小片通天木,花开正盛。每日清晨,都会有一位容貌平凡的女子前来浇水修剪,从不多言。孩子们喜欢围着她玩耍,她便一边劳作,一边轻声哼唱:
>“春风起,忆莲开,
>星儿眨眼守灯来。
>不怕黑,不怕冷,
>只要记得,就不孤单。”
没人知道她是谁,但她哼的调子,分明就是《守灯谣》的变奏。
直到某个雨夜,雷电交加,一道闪电劈中屋后古树,火光映照之下,她的影子竟拉得极长,分出九道纤细光芒,恰似九星连珠。守夜巡防的士兵目睹此景,跪地叩首,次日再去寻访,茅屋已空,唯余满园红莲在风雨中傲然挺立。
消息传开,民间再度流传起那个说法:“拾玖没走,她只是变成了‘记得’本身。”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拥抱记忆。